.jpg) 深夜,我走进一家旅馆,向前台买了两瓶酒,走进客房,斜躺在床上,怔怔地盯着墙角的落地灯。
深夜,我走进一家旅馆,向前台买了两瓶酒,走进客房,斜躺在床上,怔怔地盯着墙角的落地灯。
不是很想睡,虽然什么也没想,一时间千头万绪,像万千匹野马朝我奔来。
他打了个响指,这声音我曾听过无数遍,如今我也免疫了。
“有什么事?”我懒懒的,目光不曾朝他投去分毫。
“振作起来,做你该做的事。”
“睡个觉而已,有必要鼓舞人心吗?”
他把电水壶插上,坐在沙发上玩起手机。我招呼他,床头柜上有两瓶酒,要不要先尝尝。
他搓着手,直接对着瓶吹起来。
“你所谓的该做的事,就是这个吗?”
“酒瘾犯了,见谅见谅。”
“不可原谅。”我坐起来,也喝了两口。
我们都在游离,从彼此的视线中由清晰走向模糊。耳边依稀有叫骂声,有奇怪的歌声,还有麻将从牌桌上滚落到地板上的声音。我的背部开始发热,脑中隐隐有血往上涌。唱京戏的武生抬着脚舞着长矛,眼睛瞪得溜圆,嘴里咿呀说着词。他的脸色一半是红色,一半成了紫色,后来变成黑色,总算协调起来。
“拿酒来!”他突然吼道。
不知什么时候,两瓶酒都到了我手上,一瓶几乎已经喝光,另一瓶也喝了一大半。
“你少喝点,喝多了头晕。”
“你在说什么胡话?我半口也没喝。你现在不睡觉一个人灌了一瓶半,算什么意思?”
我的神志很难说是清醒的,发生的一切似乎都是背着我演的剧本。我感觉遭到了背叛,很难过。我很想哭,嘴角刚皱起来就觉得很荒芜,内心的荒芜。我还是先喝掉剩下半瓶吧。
他从我手里把酒瓶夺过去,这回我真要哭了,但居然转化为一股怒气,我看到他毫不理会我内心的挣扎,无情地剥夺我追求安逸的权利,对我的现状熟视无睹,却自诩正义。我咬牙切齿起来。
“你有什么了不起的呢?”
他并不回应,转身走出了房间。
空荡荡的客房,剩下了孤零零的我。
我还是不想睡,即便喝醉了酒也不想,我有心事,但是不能表达出来,所以只能想。清醒时候想会痛苦,醉了再想就很戏剧性,仿佛发生在别人身上的事,我何其洒脱。
“如果还是这样,倒不如睡觉吧。”他又回来了,真是讨厌。
“我想你需要冷静,最好不要再想无关紧要的事,你对琐事的思考已经达到一种癫狂的状态,而这显然无益于你的头脑。”他还在喋喋不休。
“你懂什么,我这是在尝试从现实中寻找出路,在我没找到一条明确的路之前,势必要不断思考,否则我恐怕连理解事物的机会都没有。”
“所以你还需要酒精来麻痹自己受伤的神经?”
“我很好,什么事也没有。”
突然我真的疲倦起来,眼皮不由自主地耷拉下来。我听到他反复的吟诵,但无法翻译成语言。咒语敲击着我的鼓膜,我假设这是他的催眠曲。
“走出来吧,或者只是睁开一条缝去看这个世界。”我听他说。
“可我只能选择一方,我不能人格分裂成两个,妥协意味着毫无选择权。”
“你本来就没有,有什么特别的吗?”
“那是过去,只要我拒绝,就不会继续。”
“你知道吗?现在的你,看起来和瘸子没什么两样。”
“至少我还可以拄拐,有些人只能用膝盖行走,他们早已认命。”
他不再开口,我也不再徘徊,很快就睡着了。
作者:贤者居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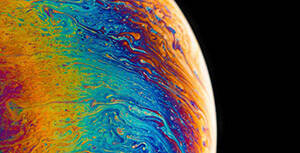


评论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