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这天温度有些高,难以忍受高温的我打开了空调,但因为心疼电费只开了一小会儿就关了。
这天温度有些高,难以忍受高温的我打开了空调,但因为心疼电费只开了一小会儿就关了。
我深呼吸室内残存的凉气,等待温度的回升,额头渐渐沁出汗珠。
真热啊,我想。拉开窗,暑气从窗洞中透进来,给烦躁的内心添上一把火。
抹去几乎流进眼睛的汗水,我走出门,不妨试着用阳光烤干我身上的汗,或许还能沾点时断时续夹杂热气的清风的光呢。
正当我站在屋檐下,看着单调的天空没有一缕云朵,皮肤毛发几乎要为刺眼的日光烧炙而炸开时,门前走过一个老人。
“不热吗,孩子?”
“不热。”我说。
老人笑了笑,头也不回的走了。
我想他应该问问自己,大热天出什么门,而不是在心底嘲弄我是不知冷热的傻瓜。
当然我什么也没说,与我无关。
我继续盯住空白如浅蓝色纸的天空,听周围静得仿佛被烤化的奶油一般无声地流动。
我的毛孔布满更多的汗珠,越积越大顺着皮肤流动成线,坠落在地染湿一个点,又迅速消失。
衣服早已湿透,但我不在乎,已经没那么热了,微风吹过还有些清凉。
我似乎忘记自己为什么要出来,像棵长在泉眼处的树,不断从树皮中渗出汁液,又迅速蒸发。
我想我在等人。
老人果然往回走,但这回他并没有之前的表示,仅仅朝我瞥了一眼,摇摇头,走了。
“你是做什么的,我从没见过你。”我朝逐渐走出我视野的老人的后背喊了一声。
老人回头看我,发皴的脸上皱纹爬满。
“你没见过正常,我是个行者。”
“行者?旅游来的吗?这可不是个好时节。”
老人笑了:“当然可以这么认为,我是旅游的,但不全是,所以不太关心时令气候。”
“所以你不热吗?”我反问他。
“热?我当然热。和你一样的热。”老人眯细了眼睛,嘴角露出似笑非笑的表情。
“不,我不热。”
“这是假话。你可以说给自己听,但千万别告诉别人。”老人准备转身。
“你这人很诚实,我能跟你一起走吗?”
“为什么?”
“因为我也想旅游。”
“你吃不消的。我从十几岁就出门了,一直到现在,里面有很多难以忍受的辛苦。”
“没关系,我也十几岁,你能忍受的我同样能忍受。你看你说你热,但我说自己不热,你说这是假话,可我说的是实话,凭这点我就能比你更能忍耐恶劣环境。“
老人哑然失笑:“或许你更擅长欺骗自己呢,就像你说你想旅游,但这种事情不是靠冲动可以决定的。正如当初我也并非想旅游而出门,而是有不得已。外面太热,你还是回去吧。”
“知道我为什么宁可在外面晒太阳也不回屋里吗?因为屋里太热。”我说。
“我看你家也有空调嘛。”
“那又怎样,不是我能控制的。”
“真有意思,难道你还没到能开空调的年纪?”
“当然不是。我只是在想,如果某天我也成为你这样的行者,还能在这大热天开空调让自己凉快吗?”
“你想磨炼自己的意志,站在日头下让身体适应高温?”
“所以我能跟你走吗?”
老人沉默了,在他迟疑的间隙,我窜到他前面,说:“走吧。”
背后的老人问我:“你知道我要去哪儿吗?”
“不知道,但我们肯定是要走出这条路的。”
“撒哈拉。”他一字一顿地说。
“那你还有很多路要走,我们得抓紧时间了。”
“你这小子,知道去哪儿吗?那是北非沙漠!”
“所以你有车吗?光凭两只脚恐怕很难到达。”
我往他身上看去,破旧的军绿色短衫,裤腿卷到膝盖的茶色长裤,不像开保时捷的人,连吉普车恐怕都不会领到驾照的可怜家伙。
“没有,不然我怎么走了大半生也才到这里。当务之急是找个落脚的地方喝水乘凉。”
我有些失落:“我还以为你真能抗热呢,要是这样走法,你恐怕永远也到不了撒哈拉,就是到了也会渴死热死。”
老人干笑了一声:“照你的理论,我徒步走到撒哈拉,早就成不食人间烟火的神仙啦。”
还没等我从失落的漩涡走出,老人从我旁边走过,很快就走到我前面去了。
“现在你去哪儿?”我问。
“没有办法,只好再到早上遇到的东家的空调下躲一会儿了,顺便再讨点茶叶水喝。”老人的声音悠远,仿佛在说另一个世界的事。
“来我家吧,我家有空调。”
“你不是没法控制它吗?”
那是遇到你之前的事了,现在我不得不学会控制它,正如你的身体并不因为忍受寒暑而益发强壮。
老人跟随我走进院子。他先走到水井旁压着水泵,嘴凑到水管口,大口喝水,因为太急而溅湿了衣衫。
他喝完水,指着井旁的卷帘门,说这是什么房间。
这是我家的车库,我告诉他里面停着一辆保时捷。
“那很不错嘛,等你长大了就可以开着它到处旅游了。”
“不,我不会开它的。”
老人发出疑惑的鼻音。
我把他领到我家客厅,关上门窗,打开空调,冷气瞬间让人清醒。
“随意点。我父母出去打工了,家里只有我一个人。”
“那你为什么不坐下来歇会儿?”老人问。
“习惯了。”我找个椅子坐下。
“平时喜欢看什么电视?”老人问。
“不怎么看,动画太幼稚,电视剧太老套。”
“听上去你好像看过很多片子。”
“没有,只是这么觉得。”我的话语里似乎有某种坚定的成分。
“能开个节目我看会儿么?”
“可以,遥控器在这儿。”
老人调到体育频道,一个穿着黑色紧身上衣,衣服背后印有金色花纹的光头在打斯诺克。
“看过这个么?”老人问。
我摇摇头。
“你应该看的,这是你应该会的。”
“为什么?”我有些不满。
“因为你不需要像我一样,走着去撒哈拉。”
这理由勉强可以接受。
我们看了会儿桌球,老人说外面没那么热了,起身要走。
“再待会儿吧,今天你也到不了,为什么不把比赛看完再走呢?”
“这或许因为我没有结束一件事的执念。”老人关上门,我能看到他脸上的笑容,那是最具迷惑性的。
上次看到他的笑,我有了做一个行者的冲动。
然而现在,我却只能望着桌球比赛目瞪口呆,冷气把我的头脑吹坏了。
我走到楼梯拐角,把电闸拉了。
天色渐渐暗下来,闷热不减分毫,但我很清醒。
我看到老人站在金色的沙堆上,一副胜利者的姿态。
他不曾有过的年轻,逐渐撕裂了脸上枯藤般的皱纹,仿佛从戏服里钻出来一个少年。
少年抓起一把又一把的沙子,又慢慢松开手,任凭沙子从手里流走。
等他玩腻了,起身走向我,用着不无调皮的语调,笑着说:“为什么不试着抓一把看看呢?”
“里面有黄金吗?”我反问。
少年一瞬间老去了,一切都恢复原状。
唯一不变的是他的笑,似乎命运从未捉弄过他。
--作者:贤者居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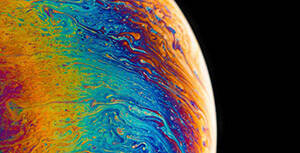


评论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