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听过很多家乡的传说,保家卫国的英雄或是杀人越货的盗贼,这些故事像风筝一样从老人的口中和故事本身的背景处远远放出来,在我的脑海中形成一点印记。随着年岁的增长,终于遥远得不成形状,变成一个浅色的点。我忘记了许多人物本身,或者不如说他们的故事也逐渐黯淡下来,不再那么引人入胜。我想我也找不出更精彩的故事,但我可以说,那些古老的传说不够精彩。那么,我想听什么呢?
麻雀停在我的肩头。
你想听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有人讲吗?
是的,我找不到那些讲故事的人了,事实上即便再让我到他们身边,他们恐怕也不乐意给我说那些能让耳朵生起老茧的文章。更何况,这时代已经足够新鲜了,尽管容得下陈词滥调,但它们终究会被新鲜事物所掩盖,乃至吞噬。
于是我躺在网上新买的廉价藤席上,想。到底什么是新鲜的呢?
很快我就睡着了。
睡梦中感觉身体下面有暖流涌动,我浮在一块琥珀似的果冻般的巨大软床上,被雾气弥漫的温泉推动着缓缓向前。我尽情呼吸着热浪,身边是青草和蓝花的清新气味。远处是一望无际的草原,有几只羊停止吃草,看我没动静,又低下头继续咀嚼。
软床停下来,一个白胡子老头对着我微笑。
能不能换个年轻的来?我嘟哝着,每次都是这么个奇怪的老头,给着含混不清的指引,也不知是专门等我的还是我该自认倒霉。
不要着急,老人捋一捋胡须,我有好东西送你,这回不再是让你神经过敏的说教,保证让你大开眼界。
我闭上眼睛不再看他,如果我有鞭子,一定抽得这软床逆流而上。
老人说,东西送你了,我走了哈。
好走不送,再也不见。
我的头皮开始发麻,因为我感到有东西正从软床的下面生长,像八爪鱼的触手,把我的头颅身躯紧紧缠裹。
这时候,我反而觉得放松起来。
别走啊老头,这是什么新式按摩床?
老头邪魅一笑,你说这是不是好东西,不需要你做什么,连脑筋也不用动一下,只管舒舒服服地往上面一躺,剩下的就让它帮你搞定。
确实不错,很快我就觉得四肢百骸都像海绵一样柔软起来,从前沸腾的脑浆现在温度居然达到负二百七十三摄氏度。
老头,既然这么舒服,你为什么不自己用呢?
老人家摇头叹息,他的颈椎腰椎都是问题,只好睡硬板床,连席梦思都不敢坐,生怕坐歪了屁股。
这时候我是该表示同情,但我几乎被这股幸福的潮流淹没,再也顾不得别人了。我大叫,我欢唱,我希望它能把我的全部都摇晃成水一样的液体,再也分不清彼此,这样我才确信自己是存活于世,而不是被造物主制作的一个具备高等智能的人形机器。
老人说,适可而止吧年轻人,你不想停下来吗?
我不知道怎么回答他,于是任凭这软床摆布。
你也许不知道怎么停下来,我来教你。你只要对它喊一声“哼!哈!”,它就像刚才送你过来时那样安静。
别说话老头,我的喉咙发出埋怨的声音。我还没享受够呢。
别搞太久,不然你会被捏成碎片的。
他的话我是信不过的,但很快我就感到心脏蹙缩呼吸急促,于是连忙喊“哼!哈!”,透明的触手从我的身体抬起,缩回到背下的软床去了。
老头再次露出诡异的笑容,怕了吧,但情况远没有我说的那么夸张,它当然不至于这么不知轻重,只是因为我提供给你这个可能,所以你退缩了。
你耍我了老头。我朝他咬咬牙瞪瞪眼,又喊了声“哼!哈!”,立刻扫去不愉快的情绪。
咕噜咕噜。我的骨节发出了愉快的气泡声。
哗啦哗啦。我的脏腑在体内肆意流淌。
我忘记了所有的哀愁,甚至忘记了老人,等我意识到的时候,他已经不知到哪里去了。
取而代之的是个英俊少年,虽然我对频繁出现过的少年也不太敏感了,但除了可以顶嘴的老人和可以欺负的少年,我并不希望再出现一个疲于奔命却一巴掌能扇死一头牛的中年人,他的戾气也许听不得我两句吆喝,“哼!哈!”一声都有可能使他想起被人颐指气使的不快经历。
我能在上面躺会儿吗?少年说。
滚一边去,没看到我还在上面吗?
少年脸色微变,这大概是愤怒。尽管我快忘记人该怎么愤怒,又为什么会愤怒了。
他不知从哪里掏出一把匕首,刀锋上的寒光几乎闪瞎我的眼睛。
我说别着急,我马上就下来,年轻人不要舞刀弄枪的,容易伤筋动骨,等你老了你就知道难受了。
少年把刀收回去了,我知道像这样的色厉胆薄之徒不会着急拼命的,他们有的东西太多,不肯轻易舍弃,而且很容易被拥有的东西搅乱了心神,忘记自己该去追求什么。其实本就不该追求什么嘛,要得多了,原有的东西也会不小心丢掉。
还要多久。少年等了一会儿,问。
快了。我回答。我又没戴表,没时间观念很正常。
不知什么时候,少年再次亮起匕首。我说有话好说,我这就下来。
少年说你要下来早下来了,我想你应该是不想下来了。
我说我忘了怎么让这玩意儿停下来了,你认识那个白胡子老头吗?
少年摇摇头。
就是他,给我一段咒语,能让这床开始和停止运作,我忘了咒语,能帮我问下或者辅助我回忆下吗?
几个字的?少年问。
好像是四个字。
芝麻开门?芝麻关门?少年说。
不不不,开始和停止是一样的话。
这可难猜了,少年开始抓头发。
几个字意思差不多。
琴瑟琵琶?魑魅魍魉?
没那么复杂,好像是语气词。
噫唏吁嚱?之乎者也?
我摇摇头,感觉都不对。
可能只有在床上的人喊了才有效果,你喊着看下。少年有些急切,年轻人不要太气盛。
我都快没气力了,喊不动了。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人。
少年又亮匕首了。
我立刻连珠炮式地把他提供的答案大声嘶吼出来,身体发出了舒服得与灵魂震颤般的呐喊。
还是不行啊,我朝他无奈地摇头。
你记性就这么差吗?少年愤愤地说。
可别指望一个享受太久的人记得自己的来时之路。我淡淡地说。
看来只能找那个老头了,能形容下他的模样吗?少年说。
他有白胡子,和我之前看到的那些老东西不一样。
是山羊胡须吗?
看起来不是很长,但是也不太短。
说话口音怎么样?
是普通话呀,其中带着点江浙方言。
你少唬人了,江浙方言差个十万八千里,你不说实话我就剁了你。
是上海口音,我惊叫起来,说话总带点阿拉、侬之类的。
少年拍脑瓜,你直接告诉他住哪儿不就行了。
我问,这是哪儿呢?
好吧,我去找。你最好赶在我找不到那老头无功而返之前想起那句咒语,不然你就等着整个进去、零碎出来吧。
悉听尊便咯,我心里想着。嘴里直喊别别别冲动,有话好说。
真舒服啊,我感觉脚趾和脚掌合成一个了,手臂和身体融为一体了。
最主要的是我的头脑,我已经感受不到它的存在了。
就好像被斩去头颅的刑天,以乳为目以腹为口。我是个殒身不恤的勇士,我体内积蓄着磅礴的力量。
来吧小子,用你的尖刀划破我的胸膛吧,这样你就能看到一颗坚强不屈的心。
想到这里,我让眼睛回到我的头顶,看了看周围。
空无一人。享受人生至乐时不需要观众。
其实何必让人知道呢?很多人都没这个契机,何况这是老头送我的礼物,和别人有什么相干?
但就这样等着那个残暴少年来杀我也不是个事,最好的方式就是找个可靠的去处,把床和我藏起来。
至于独乐乐不如众乐乐之类的鬼话,我想应该让说这些话的人降格为奴隶供人取乐。
虽然我这样想,可我一刻也不想离开这温柔乡。
好容易鼓足的勇气,轻柔的触手一捏就泄了气。
我都没脑袋和身躯的分别了,自然没有观念能干涉我的感受与行动啦。
这样几次三番作了思想斗争,我终于忍不住轻吼了一声“哼”。
于是我感到前所未有的幸福感,学着小公猪般不停哼哼起来。
感受到快乐就该表达出来嘛,即便没有观众,但这种主动释放的愉悦感,只会给享受增添几分传奇色彩。
仿佛不是因为它所以我快乐,而是我本身就如此快乐。
正如某些自以为得道的家伙会在电闪雷鸣之时指天画地,大声疾呼“独与天地精神往来”。
但单纯只是“哼”颇有种忍耐与克制的意味,于是我情不自禁地哈气。
触手便应声停下来、缩回去了。
这时候我才明白老头搞这语音模块的真正含义,他就是专为给人找不痛快设计的。
既来之,则安之。我想不妨趁此机会动手,把这软床推到一个无人知晓的僻静之处。
我刚从床上下来,湍急的水流几乎要把我冲下去。
然而在这陡然的流水中,哪怕我站在上游凭借自身重力往下蒙推,软床纹丝不动。
这时我在心底狠狠咒骂那个老头,名为送礼,实则只有使用权而无所有权。
哪怕在旁边停辆叉车也好啊,这样荒凉无人的草原,哪有什么工程队呢?
等等,草原?那我着什么急,离上海这样的一线城市远着呢,等那少年找到人,黄花菜都馊了。何况他也许会迷路,勇者通常无谋,说不定他会像误入桃源的捕鱼人一样不复得路呢。
想到这里,我继续躺到床上,享受能令人咂嘴弄舌、魂不守舍的按摩。
天旋地转,星移物换,我终于忘记了时空,只缘身在此床中了。
然而日益消瘦的身体有时让我担心,但精神力量其实可以抵抗物质匮乏的侵袭,而且我已与床融为一体,触手很快填补因我消瘦留出的空隙。
就这样,我终于忘记了自己,也忘记了床。
也会幻想自己会变成一个巨大的人形琥珀,在被人遗忘多年后从地壳中破土而出,但那时已与我没什么关系了。
至于那个少年和老人,我也不耐烦去想他们,现在来个中年大汉我也不会奇怪,他看到的是我吗?是床吗?是我在做梦被床按摩,还是床梦到在按摩我呢?抑或是中年大汉梦到被床按摩的我吗?
这样想着,我也不知自己是在犯困还是清醒,是新鲜还是陈旧了。
也许我会变成家乡的同龄人、未来的老人口耳相传、津津乐道的传说,到那时人们会怎样评价我呢?是英雄还是混蛋?无论怎样的评价,形容我的感受都是那样苍白无力,仿佛非要凭借记忆在石头上雕刻出人样,但不管多么卖力,最多不过刻出一个模样,却刻不出他灵魂的悸动。
这时候我想到那个少年,应该劝他不要拿匕首伤人,也不要去学雕刻,应该任凭刀身锈蚀,最多过个几百年会再来个诗人叹一声折戟沉沙铁未销罢了。
--作者:贤者居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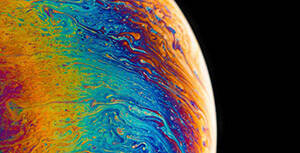


评论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