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那天中午,他用木棍在地上画了一个圈,左脚踩在圈里,问我:“我是在圈里呢?还是在圈外呢?”
那天中午,他用木棍在地上画了一个圈,左脚踩在圈里,问我:“我是在圈里呢?还是在圈外呢?”
我不想回答,因为我没想好,先不说这问题是否有价值吧,如果认为他的左脚可以代表他本人,那他就是在圈里,反之,如果他的右脚可以代表他本人,那他就在圈外。但我想他一定会否认这种荒谬的解释,正如这个问题本身。
“回答我。”他看起来不是很满意。
“在圈里。”我说。
他很快把脚撤出圈,随后撸起袖子,脸上的横肉跳起来:“你答错了,我在圈外。”
我双手护住脸,感受头顶上爆栗般的痛击。
但我想他并不是真能理解这个问题,他只是在找茬。他既不在圈里也不在圈外,他是个没有信仰的家伙。多可悲啊。
我捂着头,眼泪汪汪地回去。
我盯着尘土飞扬的路面,内心有些惶恐。倒不是担心他会再来找借口给我点颜色看看,毕竟我已经十多年没见到他了,曾经那个五大三粗的青年,早已从我的记忆中淡去。我面临着生活的挑战,每天都有千奇百怪的命运之神拿着法杖画着圈问我他们是否在圈里,我也早已习惯了抛硬币去回答他们,虽然多数情况下我都会遭到毒打,但我已不再同情这帮自以为是的蠢货,我既不用捂住练就铁头功的脑袋,也不肯再掉一滴眼泪以博得一丝怜悯。想揍就揍吧诸位,鄙人奉陪到底。
突然,背上传来碰撞的痛感,一个铝制水壶从我身上跌落。
“烧壶水,把头脸好好洗洗,看你成什么样子。”女人把干毛巾搭在我的肩头,往我怀里扔了块硫磺皂。
“阿兰,我真没用,配不上你。”
阿兰沉默着。时间在流逝,路上的沙石随风浮动,烟尘扑面而来。当我回过神来,女人早已离去,铝壶底部裂开,毛巾变成破烂抹布。这世界在沉睡,等待着死亡的朽烂。
“虽然这么说不怎么道德,”她临走前对我说,“但你确实就是一个废物。”
我很想搞点酒来喝,红的白的啤的都行,不是为了附庸风雅,纯粹是要一种感觉,醉死方休。没有酒,那就装作已经喝过,躺在床上,想点过去窘迫的经历,脸红得和喝醉了一样,也便当作自己醉了。然而什么都想不起来,只觉得现实空空荡荡,然而却有种写意的浪漫。不,不是,我在欺骗自己,这里面一点也不浪漫,只是我在逃避思考,拿着自以为是的知道当作置身事外的护身符,全然忘记自己一直都在以动物或者野兽的形态在世间裸奔。
“这里,是哪里?”我喃喃自语。
“管他是哪里。”我脑中突然浮现这样一句谶语。
于是我起身从床头柜里翻找,里面有许多针头线脑,纽扣和布条散乱无章。但我不需要这些,衣服上有破洞,琐碎的人或许要补,但对我而言,则是可以完全忽略。然而心灵上的洞,不是它们能帮我粉饰的。
我拿起那本书,透着神秘的气息,蓝色的幽光从边缘散开,我似乎还能闻到烟草的气味,虽然更多的是一股霉味。我开始阅读其中的字句,断断续续,如同在微雨天张开嘴品啜雨滴的滋味。我看不明白,从来都是这样,心里想着什么都看破了,什么都管不着了,结果连最简单的词句都无法理解。我有心事?可为什么说不出?我内心空洞得很,却连简单的精神填补都进行不下去。
“那么,你在哪里?”
“我看下地图。”
没有地图,风沙弥漫,我的头发和指甲里都是尘土。也许会有东西指引我,比如说一只蚂蚁,它的活动边界是我可以轻松走到的地方,但我不会和它争论路标应该设在哪里,何况我们都不足以做对方的向导。
那我就自己走。
邻居家的老头问我往哪里去,我说没事,只是随便逛逛。他点头,说不然进屋坐坐,打打牌?我同意了。他问我渴么?我点头,但他并没有给我倒水,只是像巫师那般从棕色麻布里拿出一叠牌,用极度笨拙的手法洗牌————将所有牌散在桌上,肆意地抹动,看得出来他有推油的本事。我等了很久,觉得他很无聊,并不是真想和我打牌,于是起身准备走。
他突然停下,抬起头看我:“洗好了。”
我看到他因为连续抹牌而疲惫颤栗的双手缓缓地将牌合在一处,说:“两个人能玩的东西有限,抽牌比大小吧。”
我没有异议,反正怎么都一样。
他把牌递给我,让我先抽。我拿起第一张牌,是老K。他接着翻开第二张牌,是小王。我输了。
我看着他牌面上那个灰色小丑,心里不禁感慨,时代真的变了么?庄严肃穆不如滑稽杂技?
然而我也是认同的,我并没有拒绝这种另类的规则,相反,这正是公平的体现,至少他还洗了牌。
我准备揭开下一张牌,突然一个女人走进来。
“阿兰?”我有些惊讶。
“别叫我小名,我觉得恶心。”女人冷冰冰地说,“我准备结婚了,下个月中旬,你到时候可以来。”
说完,她头也不回地走了。
我想我是不会去的,她不是诚心邀请我参加,而是对她不堪过去的一种决绝的羞辱。
我掀开牌,是红心A。
老头咳嗽了两声,仿佛只是清嗓子一般,或者想用寻常的方式化解尴尬气氛。他突然说,其实他年轻时候也遇到几次这种事,看开了就好。
我提醒他开牌。
是大王。
我把牌堆翻过面,在桌上一字抹开,随后惨然一笑,离席要走。
老头说他学过占卜,我是命犯桃花,只是暂时被小鬼压住了而已。我说如果你出老千的手法再高明一点,我就心悦诚服了。
关键是老头,咱们又不来钱,你图我什么呢?
“年轻人火气大,遇到点事就要反抗,或者就一撒手就跑,虽然好玩,但是毫无用处。”
但是你耍我了。
老头笑:“这不能叫耍你,我们又没来钱,你输了也不算我强迫你的,我让你抽牌,但又没让你按顺序抽,你自己不变通,还要怪我咯?”
关键在于他给我的牌象征意义太重了些,我觉得很讽刺,虽然没见过阿兰的未婚夫,但想必比那张大王牌面上的小丑好不了多少,只是身上附加了点东西让他得以哗众取宠。
话说回来,老头你真学过占卜?能算下我能挣到钱么?
老头又用极度拙劣且卑鄙的手法洗了回牌,让我抽,这次我抽了张中间的牌,他让我先不要看。
随即拿了一盏油灯摆在桌上,掩上房门,屋里只剩下油灯微弱的光。
老头把剩下的那叠牌放在耳边拨了一回,随后把一张牌放在火上引燃,抛到地上,连续几次,颇有种巫师做法的意味。我看到火焰在地上跳跃,又瞬间熄灭。老头突然念念有词,说了许多奇怪的咒语,脸上忽苦忽笑,或做出各色鬼脸。我看得有些呆了,坐在原地不知所措。
老头烧光了手中的所有牌,向我伸出手来。我把手里的牌给他,他接过牌,往油灯上一扣,灯灭了,屋里一片漆黑。
“老头你干什么?”我错愕地问。
“你凭什么认为你手里的牌能给你带来好运呢?为什么不是像其它人那样被毁灭,或者主动结束这场罪恶的游戏呢?因为这是你选的,所以有特别之处?纵然它能代表你的意志,它能代表你吗?”
我脑中一阵眩晕,目力所及,黑暗中似乎藏着一具骷髅,正在对我摄魂般地灌输某种极其现实的观念,我想抵御,但发现从前包括现在我都是这么认为的,只是不再严肃,把所有施诸自身的拷问当作没来由的狗叫。然而如果没有能代表我的东西,那我是什么呢?从戏谑中赢下所有牌,然后自欺欺人地全身而退?
但我不能挪动半步,我的命运似乎早已注定。
--作者:贤者居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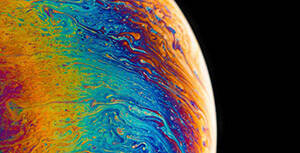


评论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