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机器的这端走到另一端,差不多需要五分钟左右。我穿过狭长的甬道,在一颗零件旁停下,用手里的铁锤敲敲打打,发出叮铃的响声。这声音在机房里回响,空气静得出奇,使得我的举动造成了不小的骚乱,虽然没人指责我。
从机器的这端走到另一端,差不多需要五分钟左右。我穿过狭长的甬道,在一颗零件旁停下,用手里的铁锤敲敲打打,发出叮铃的响声。这声音在机房里回响,空气静得出奇,使得我的举动造成了不小的骚乱,虽然没人指责我。
一位长得很成熟的女士闻声而来,她脚步轻得像蚂蚁抬步,见到我一身工装,脸色立刻变得和蔼起来:“师傅,请先到这边做个登记。”
我不需要登记,这是我的权利。
她的脸色有些不悦,但还是尽量保持温柔的语气:“不好意思,凡是来这里的都需要登记,不然我们这边不好交代的。”
“你们这机器坏了多久了?”
“师傅,请您不要岔开话题,我们可以先记一下名字,填一下临时工号,然后再开始接下来的任务。”
“我猜你还没转正吧,小妹妹。这么着急记录访客,是想早点回到工位上歇着么?”
她带着几分严肃和稍显刺耳的语气说:”师傅,请尊重我的工作,我们上级要求每个人进来都需要登记,如果您不想走流程,那请您离开这里。“
我笑了笑,把铁锤放进工具包里,说:”我不想走流程,当然也不想听你的话离开这里喽。如果你执意要我走,那没办法,你们上级一定会让你卷包袱滚蛋的。“
她很生气,立刻打电话给她领导:”王主任,有位师傅来这里不登记名字和工号,我现在没办法处理了,希望您能来一下。“
电话那头不知道说了什么,接下来这位稍显成熟的女士开始连连点头答应,后面几乎微笑起来。她挂了电话,嘴角上扬,说:”主任说了,你可以走了,下次耍大牌的时候记得看看场合,不是所有地方都需要你这号人物。“
我回敬她:”你这号人物普天下多的是,少狗眼看人低了。要是我走了,你别后悔。“
”我可一定会后悔死的,和你这种人浪费口水,是我做过最愚蠢的事。你要是再不走,我可要叫保安啦。“
我拍拍屁股走了。
我点了一杯伏特加,坐在吧台边上慢慢喝。音乐柔和,酒也柔和,在这秋风也要沉醉的夜晚,我回想起那个厂房,那个姑娘。电光火石间,心里好像什么被触动了一样。我开始醉了,一杯也要把我醉倒,即便在这无聊的酒吧听着平淡的曲调,我的身体几乎飘上了天,灵魂开始俯瞰大地,望着所有睡着了和醒来的人,我笑。我什么都不去改变,到底是因为不能,还是不屑?我懒得拷问自己,拷问意味着思考,而思考正是我们所摒弃的,因为我们早已习惯了一种生活,一种舒缓的节奏,像在浴盆里用温水浸湿肌肤,像用手指轻轻一点就塌掉的酥软蛋糕,美女的裙摆在幽暗的聚光灯下摇曳,人们都卸下面具露出孩子般的笑脸。有人指着我说:“瞧这醉汉,如果不是脸红得和屁股一样,我还以为他要拿扳手调酒呢。”我把扳手从裤袋里掏出放到吧台上,继续喝着酒,那人就收起了笑脸,或许出于对我职业的敬重,为此我也要敬他一杯。
但我已经不能再喝了。出了门往右走了几步,在一家便利店前停了下来。我不进去,坐在台阶上抽了支烟。店员出来说我挡住他们的大门,我反诘他怎么这么肯定晚上还会有客人来?他骂了两句,回到了收银台。我等烟抽完,接着在门口刷手机,后来有些乏了,就横躺在门口的瓷砖上睡觉。店员没再出来,我做着梦,脑子里一片空白,但依旧是很美的梦。
不久听到警车的声音,两个年轻警察站到我旁边,让我醒醒。店员打开玻璃门开始陈述情况,我伸了个懒腰,左右看了看,说:“我这么睡到这儿了?”警察就开始对我进行批评教育了,我说喝得人事不省,还以为躺在出租屋的床上呢,不知道谁把我搬过来的。店员说我胡说,我当时清醒得很,还在他门口耍无赖。警察和稀泥似的劝了一回,让我早点回去休息,以后少喝点。
我翻开笔记,里面都是之前记的乱糟糟的公式,现在很多已经回想不起代表的含义了。记点未来能读懂的吧,我想。考虑了半天,我终于在空白的一页写上一句“a+b=b+a”。想想又不对,在上面画了个圈,打了个问号。合上笔记,我露出满意的笑容,有人在暗处打了个响指,声音有些沉闷,大概不在我的衣柜,那里只有老鼠和蟑螂。我喝着浓茶,嘴里念叨着“严谨但不够实际,实际但不够严谨”,耳边传来劣质洗衣机的强烈震动,汗液混杂着尘土从我的脖子淌到肚子上,洗出几条小路。我望着桌上那盏台灯,是该换了,但不一定是现在,或许应该是昨天,明天已经迟了。零点的钟声已经敲响,房间里没有摆钟,但是脑子里荡起了一圈圈的涟漪,有人从水里出来,露出尖利的爪牙;有人从水面上沉下去,比水还要柔顺。但他们都将化为灰烬,时间不曾为他们停留,记忆迟早会被水冲刷干净。
早餐我买了一张甜烧饼和一份土豆丝卷饼,边吃边往机房那边走,阳光很好,虽然已经入秋,天气还是有些燥热。我身穿灰色工装,斜挎着工具包,身心轻松,接下来只要完成工作任务就万事大吉。
正当我检查某颗零件的状况时,一个女的让我去签字,我签完之后继续检查机器的零部件。这对我来说不算容易,但好在经验还算丰富,所以也不需要慌,大不了再请教别人么。乍看这台机器极其庞大,但只要动点脑筋看清全部构造,就差不多能分出功能模块来,虽然我挺讨厌看这种明显带有设计缺陷的机器,但身为即将踏入专业领域的维修师,不管什么菜捏着鼻子也要往肚子里咽。我不太清楚这种老旧设备现在还有多少厂家在用,虽说存在即合理吧,但总感觉是在考古,而且可以从这些锈迹斑斑的构造里闻到比我身上还要浓烈的恶臭,我一边嫌弃它的陈旧腐朽,一边又佩服它生命力顽强。我从一颗零件摸到另一颗零件,手上沾满了机油,心里倒是愈发清楚。两个小时后我打电话给王主任,说机器已经修好了,电话那头向我殷勤致谢,并邀请我留下来同他共进午餐。我不太喜欢,我有自己的事要做,不想被别人占用宝贵的时间。
我所说的事,就是走马路。即使是大热天,我也要走个十几公里,走得身上直冒热汗,走得口干舌燥腰酸腿麻。这可以称作一种苦修,但我不信教,只是因为时间太多又不信上帝,所以不得不抱着实用主义的心态走这全然无用的路。走路的时候会思考一些东西,脑子不断反刍,有时会为自己曾经的表现、不经意说的某几句话而喜悦,有时会想起遭受某种不公的待遇而嗔怒。虽然时间过得很快,但一直在走,所以不算什么也没做,起码大半天过去也能明确自己走过的里程,而这似乎是一种证明,比起坐在出租屋里毫无痕迹的白日梦,我宁可在行走中完成自己的畅想洗礼。我知道自己不起眼,外表看上去和叫花子没什么两样,好在我还有证明自己身份的工具,但那是否会被误以为走到穷途末路的土匪强盗也不一定。到中午太阳已经很毒了,但我还是继续走,虽然看到了很多东西但什么也没在我脑海里留下一丝痕迹,我的日常已经够我感悟人生的曲折,而历尽千帆,眼前不起眼的东西丝毫吊不起我的胃口,哪怕走进灯红酒绿,哪怕眼前就是人潮。我渴望的,就是不断走下去,如同夸父一般,直到最后倒下,那会被别人耻笑,但于我而言则是一种幸福。
走到黄昏,我找到一家酒吧,打算喝点什么解渴。我一般喝超市里四块一大瓶冰镇冰红茶就够了,但今天我要奢侈一把,仅仅因为想到夸父一味追日而没机会尝到自己死后化做的桃林里结的桃子就觉得可惜。当然我不爱喝桃子味的酒水,那样还不如喝饮料。我给自己点了杯伏特加,随着柔和的音乐,我的疲劳似乎得到了缓解,神经也逐渐放松起来。我想到自己的工作,虽然枯燥,总算还能给我一点满足感,也是活着的凭证。我确定自己是需要给养的,而不是像犁田的牛一样只用吃草就能劳碌至死,所以该享受的时候也不能太拼命。也许我该整一套干净体面的衣服,毕竟进的是略显高档的地方,不过穿得再好也是给别人看的,钱包也不会因为装成一副老板样子鼓起来,所以我不在乎,也懒得向别人公布自己目前渴望放松甚至是放纵的心态。但总有不识趣的来取笑我,但我打算喝完这杯就走,未来怎么样还不一定呢,我改变不了别人的浅薄,也无心让别人意识到我的深刻。
走出酒吧,我的心情开始烦躁起来。也许因为刚才的酒有些烈,我不胜酒力,也许因为那句刺耳的调笑,和别人肆无忌惮的嘲讽。我迎着秋风走到一家便利店门口,想抽根烟,顺便醒醒酒。店员开门说别挡道,我的屁股往旁边挪了挪,他便不再说什么了。抽完烟我想起家里蟑螂和老鼠太多,不知道有没有驱老鼠蟑螂的香或者药,毕竟实践证明二手烟是毒不死这帮杂碎的。店员很遗憾地表示没有。我想进来就问这些似乎不太体面,不买点东西也对不起我今晚在酒吧里的消费,所谓今朝有酒今朝醉,干脆再来个大手笔。斟酌再三,我看到角落里的一盏台灯,也许以后我晚上可以读点或写点什么,床头灯太暗太闪了应该摆到会所去,即便是刷手机也该有个稍微正常点的环境光源。
我摊开笔记,上面密密麻麻爬满了乱七八糟的公式,这是我近年来为了维修做的功课,现在很难说清哪些是真正工作需要的,作为字典也显得太潦草而不堪卒读了。我掀起一页,总算看到能认清的符号,但这不知道是哪个小学生在我笔记上的鬼画符,是否因为门锁坏了偷偷跑我出租房里搞恶作剧?我想了想,在“a+b=b+a”旁的问号上涂上几条线,然后郑重其事地在等号上划上一条斜杠。这时手机上显示零点,衣柜里恼人的耗子又在吱吱叫了。
--作者:贤者居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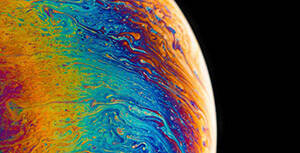


评论区